(編者按:這篇文章很長,作者從學術立場出發,嚴肅地從縱向到橫向,分析歐美中俄近代以來,作為主導世界秩序的主要勢力的發展、推進以及轉變,作為大陸學者,他對全球未來的預測更為接近中共官方的視角,這雖然跟歐洲之聲的觀點和立場相左,但本文依然有參考價值。)
以大歷史和長時段的視角來俯瞰當下世界政治的進展,常常能夠讓人們對當下事件的意義形成更深刻的理解。我們正在親身經歷20世紀與21世紀之交的全球轉型過程,這是一個少則經歷了兩個多世紀、多則長達五百餘年的宏大歷史進程的關鍵轉折時刻。多年來複雜環境之下所導致目前的俄烏危機,以及與此相關的包括中俄在內的當代大國關係,都以全球轉型為整體背景。
俄烏危機,作為冷戰結束後最大規模、已持續兩年的地區衝突本身,猶如“催化劑”、“振盪器”與“反光鏡”,深刻地反作用於全球轉型,全面、系統且以內生的方式塑造著包括中俄在內的對外戰略與大國關係的未來形態。在此過程中,中、俄、美、歐等大國關係的複雜互動,既直接影響俄烏危機前景,也勢必深刻左右全球轉型的內涵與走向。
由此可見,我們所面臨的是一個前所未見的、古今關聯的、內外交織的挑戰與建構並存的時刻。需要以深刻的理論研究和創造性思維加以探索和解釋。
本文嘗試探討以下三個正在運作中的國際現象之間的相互關係:第一,作為歷史長過程的全球轉型及當代啟示;第二,世紀之交以來全球轉型與俄烏危機的相互作用;第三,轉型與危機下的中俄合作。希望本文的初步探索能為理解全球轉型提供新的思路。
一、「國際秩序週期演進」問題的爭論及其啟示
在所有圍繞全球轉型而展開的研究中,國際秩序的未來走向是研究者關注的焦點。近半個世紀以來,在國際政治經濟學、社會學和歷史學等領域有了系統性、開創性的相關研究,也觸發了引人深思的爭議。有必要對多年的相關探索作一番簡要回顧。
大體而言,至少有三類以國際秩序歷史性更替為主要對象的國際研究。
第一類研究,以世界歷史與國際戰略學家、同時也是具有難以比擬的豐富外交實踐經驗的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博士為代表。在他看來,歐洲三十年戰爭之後,1648年出現的威斯特伐利亞體系改變了人類社會僅以「帝國一統」或「宗教一統」的傳統秩序觀,「威斯特伐利亞概念則把多樣性當作起點,把各國視為客觀存在的現實,以此吸引了情況各異的國家共同探索秩序。到20世紀中葉,這一國際體系已涵蓋地球各大洲,至今仍是國際秩序的骨架”[1]。基辛格是這樣解釋何以歐洲能使「多元化成了世界秩序的典型特徵」的,他說:「這並不是說,歐洲各國君主比其他文明的君主更能抵制征服帶來的輝煌的誘惑,或對一個抽象化的多元理想更加執著。歐洲的君主只是缺乏把自己的意志強加給他人的實力。隨著時間的推移,多元化成了世界秩序的典型特徵。」[2]

在基辛格的敘事體系中,儘管此後歷次國際秩序演變都沒有那麼自覺地達到威斯特伐利亞體系的“多元化”背景下的那種“克制”,但是,1814年維也納條約、1945年雅爾塔協定、直至冷戰終結等歷次國際秩序構建的實踐表明,多元與多極結構確實一而再、再而三地通過維持均衡,避免了全面戰爭。例如,維也納體系雖不那麼“民主”,是君主體制或半君主體制的歐亞諸列強之間的“大國協調”,但卻避免了全歐規模的大戰爆發,大體維持了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所說的「百年和平」。而雅爾塔體系雖經歷半世紀可怕的冷戰,但畢竟還是維持了美蘇等不同社會制度大國之間的劃界對峙、共處並存。包括冷戰終結後,雖然美國一度單極獨霸,但在世紀之交轉向多極、多元的趨勢出現之後,世界各國人民依然在此基礎上保持著對於和平發展的期待。
總之,基辛格從對國際「多極」與「多元」實際狀態的承認與尊重開始,經由精心打造的「勢力均衡」策略的運用,以「合法性與權力相統一」的理念為基礎,追求在「從來不存在一個真正全球性的『世界秩序』」的國際環境中,去實現「不同類型的世界秩序」的各種抱負間的和平共處。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尼爾·弗格森(Niall Ferguson)認為,基辛格不僅是個現實主義者,而且是個理想主義者。雖然這一說法與傳統國際政治理論的含義並不一致,但這項見解是很有道理的。[3]
第二類,被國際學界視為從事“現代世界體系”,或“世界秩序演進週期”的研究者群體,其中包括法國年鑑學派代表性人物費爾南·布羅代爾(Fernand Braudel),以及義大利「世界體系理論」代表性學者喬萬尼·阿里吉(Giovanni Arrighi)。雖然這一派內部存在爭論,但筆者認為,這一派別理應包括《現代世界體系》四卷本作者、美國左翼歷史社會學家伊曼努爾·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
這項派研究的核心觀點是,在近代以來國際秩序多次更替的關鍵時刻,都出現過西方霸權國家為核心的資本主義體系的興起。17世紀歐洲“三十年戰爭”的結果,不僅是基辛格所說的“歐洲內部的多元化”,而且是荷蘭共和國的異軍突起。法國大革命後拿破崙戰爭的結果,不僅是維也納體系的列強並存,更是表現為大英帝國的崛起。第二次世界大戰造就了一個五大國並存的聯合國安理會,但是美國不僅取得了較之當時蘇聯更具主導性的世界霸權地位,而且即便在冷戰終結後世界走向多極、多元之際,美國還是當今最強大的霸權國家。[4]換言之,世界秩序更替之下的常態,乃是多極化與國際力量中心的並存。
在《現代世界體系》2011年英文版第一卷序言中,沃勒斯坦有一段自我表白:「當時我有一個糟糕的想法,即透過研究在16世紀’新興的’國家是如何’發展’的,也許能夠更好地理解20世紀’新興國家’的發展軌跡。這之所以是一個糟糕的想法,是因為它假設所有國家都將遵從相似的演進路線,…”[5]儘管沃勒斯坦後來對自己原先的想法有所修正,但他堅持從「世界體系」的角度,而不是單一國家角度來觀察這個問題。沃勒斯坦批評韋伯(Max Weber)的社會學理論,尤其不贊成「新教倫理產生資本主義」的觀點,他說:「所涉及的價值觀是伴隨著正在發生的經濟轉型而發生的,而不是在它之前發生的。我提出,只有通過將各個國家置於他們彼此的關係中來考察,才能理解為什麼一些國家在生產效率和財富積累方面成為領先者。”[6]同時,沃勒斯坦認可斯蒂芬·門內爾(Stephen Mennell)對「世界體系」研究的評估。門內爾指出:這「實際上是從歷史方面反駁大衛·李嘉圖(David Ricardo)揭示的、永恆存在的’比較優勢規律’的一次重大努力。它表明,最初在各種社會和經濟之間相互依賴關係中的不平等程度是多麼小,但隨著時間的變化,不平等程度被不斷加劇,以致產生在今天被委婉地稱為’北方’和’南方’之間的巨大差別。」此外,沃勒斯坦與布羅代爾儘管有分歧,但他們都認為,「…沒有提供證據證明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自主性,證明它可以完全脫離國家和政治。相反,它們證明,國家事務和資本主義事務是密不可分地連結在一起的,它們只是同一歷史發展過程的兩個面向或部分」[7]。可見,沃勒斯坦、包括法國年鑑學派的觀點之所以會引起爭議,是因為這已經不僅僅局限於世界體系的演進更替問題,他們已經系統而內在地對西方政治經濟理論的最基礎的部分提出了質疑與挑戰。
值得注意的是,喬萬尼·阿里吉繼承了布羅代爾的觀點,更有系統地強調,每次霸權轉移都會同時出現以下現象:
第一,全面戰爭——例如伴生威斯特伐利亞體系的“三十年戰爭”,導致維也納體系的拿破崙戰爭,以及產生雅爾塔體制的第二次世界大戰。
第二,從金融擴張到衰退──這裡指的是,並非如傳統觀點,整個資本主義體系數百年發展過程是從工業資本主義,經商業資本主義,然後發展到金融資本主義的。事實上,從荷蘭共和國、大英帝國、直到美國霸權的每一個霸權週期之中,都不同程度地經歷了從工業資本主義、商業資本主義、直到金融資本主義的循環起落。

第三,以領土為基礎的強大國家-「傳統觀點是資本主義和市場經濟或多或少是同一件事;國家權力是同這兩者對立的。布羅代爾(作者註:也應包括沃勒斯坦)則認為,資本主義從其出現到擴張完全依賴於國家權力,並構成為市場經濟的對立面」[8]。事實上,年鑑學派的「市場經濟不等於資本主義」的思想,深深影響了中國改革開放的過程。喬萬尼·阿里吉總結:每次國際秩序的更替,都是以上所言「全面戰爭」、「金融從擴張到衰落」、以及「以領土為基礎的強大國家」這樣「三位一體」的產物。毋庸置疑,阿里吉對世界秩序更迭的歷史總結,直指當下的全球轉型。
尤需指出的是,2009年,阿里吉在為自己1999年所寫《漫長的20世紀:金錢、權力與我們時代的起源》的後記中指出,“盡管西方主導的全球帝國的可能性仍然存在,但與15年前相比,今天以東亞為中心的世界市場社會似乎更有可能是當前全球經濟政治轉型的結果……中國已經開始取代美國成為東亞及其以外地區商業和經濟擴張的主要驅動力”[9]。
第三類觀點,以德國歷史學家於爾根·奧斯特哈默(Jürgen Osterhammel)為代表,這是一位向上述“世界體系”與“世界秩序更替周期”理論發起挑戰的權威歷史學家。他在2010年出版的三卷本名著《世界的演變:19世紀史》的中文版序當中寫道:“我之所以決定撰寫一部由無數微小關聯構成的歷史,是因為與那些闡述宏大理論的著作相比,這類歷史寫作迄今較為罕見。”[10]奧斯特哈默不太願意與之為伍的“宏大理論”類歷史著作,首先指的就是伊曼努爾·沃勒斯坦的著作。他在稍後的論文集《全球史》中曾這樣表示:“世界史與一種向歷史學開放的社會學之間的上一次交鋒發生在1970年代和1980年代,是在‘世界體系理論’的號召下發生的。世界體系理論的創立者是美國的非洲專家兼發展理論家伊曼紐爾·沃勒斯坦,他屬於當時世界上頂尖的社會科學學者。他通過與法國大歷史學家布羅代爾的對話,也獲得了較高的歷史學聲譽。由於沃勒斯坦的理論比較機械,而且與特定的術語捆綁在一起,所以只有少數歷史學者接受沃勒斯坦及其追隨者所捍衛的正統形式。”[11]而奧斯特哈默對布羅代爾的態度更為含蓄。他曾這樣寫道:布羅代爾“在論述15—18世紀資本主義與物質生活發展史的著作中,的確是把整個世界都拉進了視野,仿佛在他看來,這樣做是理所當然的。布羅代爾小心翼翼地避免讓自己陷入關於世界史問題的爭論,他所感興趣的話題並不是這一時間框架內的科技、貿易結構或世界觀的重大轉變,而是社會以及社會內部網絡的運轉方式。令人驚訝的是,布羅代爾式的全景式視角並沒有得到大多數人的仿效。”[12]

奧斯特哈默的表達盡管委婉,但是立場很清楚。第一,他明言自己的重要著作“放棄了以國家、文明或陸地空間為標準的地域劃分”。顯然,這與布羅代爾、沃勒斯坦所強調必須將國家、文明、地域空間與資本主義發展合二為一地加以觀察與分析的觀點相異。第二,奧斯特哈默坦承,他“強調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的重要性”。[13]很明顯,這與年鑒學派與沃勒斯坦批判殖民主義的立場明顯不同。第三,從方法論上說,奧斯特哈默不主張過多地強調歷史科學應具有預測功能。例如,阿里吉曾認為,20世紀與21世紀交替時期之後的東亞有可能成為取代歐美的世界主導性力量,而奧斯特哈默則在他的新作《全球史》中比較隱晦地寫道:“沒有什麽可預測的:亞洲的未來就是它的過去。”[14]在他看來,亞洲以往“停滯不前”的歷史,勢必預示其未來的難有進步。此外,盡管奧斯特哈默並不完全拒絕近現代世界歷史發展存在著時空統一性,甚至對某些他所認為的世界歷史中重要而共同的節點,還做過系統論證,但是,他與年鑒學派和沃勒斯坦的區別在於,他並不主張把世界歷史過程視為一個相互關聯、全球統一的過程;他也不太相信,如此宏大、複雜、多樣甚至會出現反復的世界歷史進程會受某種“規律”(布羅代爾對此非常強調)的先天命定式的支配。相反,他更多地關注細節、局部、多樣性、偶然性、非同步性、多線條線,而不是宏觀整體、進程劃一或世界歷史的單線條發展。
如果對上述有關“國際秩序周期演進”的多種不同見解作一簡單歸納,並且更多關注其相互補充、相互修正的內容的話,那麽,擬提出以下初步的判斷:
第一,世界歷史進程並非單線演進,而是既充滿偶然性、多樣性、曲折性,但在不同時代、不同領域、不同層次上又確實存在著整體關聯、辯證統一、螺旋式演進的歷史趨勢與時代特征。國際秩序的周期性演進並非臆造,乃是一個並不外在於人類的能動精神、主客觀因素相結合、並不斷受到歷史啟示的複雜進程。
第二,近代以來,國際秩序演進的兩個基本特點是:一方面,每次國際秩序的更替既走向多極、多元趨勢,但也存在著全局意義上的力量中心。“多極”與“力量中心”並存,是理解國際秩序演進的關鍵。另一方面,每次國際秩序更替幾乎都是“全面戰爭”、“金融領域從擴張到衰落”、“主導性國家出現”這樣的“三位一體”的產物。這對觀察當下國際秩序演進提供了一個十分重要的參照。
第三,20世紀與21世紀之交的國際秩序演進與更替,可能會出現“轉軌”。也就是說,並非如以往那樣,僅有西方文明國家才可能主導世界,而是前所未見地出現了西方文明圈外的力量中心在一定條件之下可能成為更替候補者的戲劇性變化。
第四,不可忽視的是,需要從更加廣譜、多元、多線條發展甚至會不斷出現反復的維度,從更多領域、更多案例、更多學科知識的反覆思辨中,系統周到地思考未來的變局,而非沈湎於缺乏依據、主觀隨意的所謂“預測”。在思考國際秩序更替的複雜問題時,既避免條件尚不成熟或代價過大的“提前上位”,也高度警惕國際亂局中原主導國家影響力在關鍵領域的“已經缺位”。全球轉型進程的高度不確定性,規定了這一態度的必要性。
二、當代全球轉型與俄烏沖突的相互作用
俄烏沖突是世紀之交以來全球轉型的一個“鏡像”。這場危機映射出這一關鍵時刻全球轉型所面臨的各種問題。需要通過對危機的透徹分析,全面客觀地評估這場沖突對於當下全球轉型的作用與影響,客觀鑒別轉型與危機互動中的心理觀照與敘事體系的真偽正誤,深入發掘這一階段全球轉型進程中的深層結構性變動走向,全面梳理危機與轉型中的關鍵現象——全球化進程的實際趨勢。唯有如此,才能對轉型中的挑戰作出回應,也才能真正為俄烏危機這一類大規模沖突找到出路。筆者認為,俄烏沖突至少從以下四個方面深刻影響著當代全球轉型。
(一)沖突加快全球轉型的節奏,但催生“決戰心態”
俄烏沖突的爆發大大加速了全球轉型的演進節奏,不僅無情揭示出各類矛盾,也催化各國“決戰心態”湧動。
從縱向線性視角看,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的巴里·布讚(Barry Buzan)教授提出,從19世紀西方的殖民化、二戰後美國主導世界事務、冷戰後美國甚至曾一度稱霸世界,一直到20世紀與21世紀交替之際一個“去中心化”的歷史潮流的出現,標志著一個長時段的全球轉型過程逐漸成形。[15]

而從橫向系統結構看,正如旅美俄羅斯學者安德烈·茨岡科夫(Andrei Tsygankov)所言,全球轉型是指:國際秩序變更;國內體制沿革;連接這兩者的對外戰略與國際關系,這三種結構進程的系統綜合體。[16]
從沖突各方的動因來看,俄烏沖突不言而喻地從“縱向”與“橫向”兩個角度同時作用於“全球轉型”。
就國內轉型來看,俄羅斯與烏克蘭代表著兩種不同內涵的社會轉型,前者強調本土,後者則著眼歐美;前者固守本土自主,後者奔向“民主陣營”。道不同,不相為謀。俄烏沖突,緣起內部體制選擇的差異,勢必進一步強化以內部體制的構建作為解決外部沖突的基礎。
從區域角度看,2014年筆者曾經在《歐洲研究》撰文,提出歐盟與歐亞經濟聯盟各自推進的一體化,兩者雖都符合市場原則,也在不同程度上關注內部平等,但兩者對烏克蘭的你爭我奪,體現出各自為政的排他式區域建構的缺陷,不僅成為克里米亞危機的誘因,也勢必作用於未來歐洲地緣經濟、政治、安全結構的形成。[17]
從全球層面來看,俄羅斯要終結單極世界,但美歐則竭力維護西方主導地位。誠如普京總統2023年10月5日在瓦爾代論壇上所說,“特別軍事行動與領土占領無關,甚至與地緣政治無關(按筆者的理解,這里的‘地緣政治’應該指的是北約東擴),而是事關國際秩序的重構”[18]。然而,對於西方世界來說,國際秩序更替的問題,不僅事關利益,而且關乎榮耀。奧巴馬曾於2014年5月在西點軍校畢業典禮上明言:“我們的軍隊天下無敵,……我們的經濟活力仍居世界第一,……我們是各國有史以來無人能及的聯盟軸心。……美國始終是一個無可取代的國家,上個世紀如此,下個世紀亦是如此。”[19]從這一立場出發,美歐重啟結盟,強勁反制俄羅斯,實屬勢所必然。事關國際秩序大局的兩相對立之下,雙方最終在國際建構最為脆弱的安全領域——以烏克蘭為聚焦點的俄羅斯與北約關系上——爆發軍事沖突。從後果來看,這場沖突揭示出了現有國際體制中的結構性弊端——各類全球以及區域性組織的現有功能尚無法阻遏類似俄烏沖突的大規模危機。因此,相關領域的改革、提升與強化勢在必行。否則,世界將不得安寧。
同時,這場沖突促使人們更加全面地考慮:如何調處局部變革發展與作為環境的外部世界的相互關系。比如,一國有權獨立處置內部事務與外部發展問題,但如何與外部國際環境相協調?又比如,一國有權選擇自己的外部結盟關系。但是,一國處理自己事務的獨立自主原則與地緣政治所強調的保持大國間適度空間隔離與緩沖的客觀需要能否共處?再比如,一國領土主權完整的國際公認準則,與尊重一國內部民族自決自主權限,這兩條國際法基本準則如何統一?在科索沃危機與俄烏沖突這兩場危機上述原則之間出現對沖與爭議時,人們是怎樣調處的?總之,早先階段全球轉型所強調的改革發展、獨立自主的通行原則,在國際環境發生若幹變化後應如何運用於不同的場合,使之減少外部阻力,避免國際沖突?顯然,俄烏沖突以十分尖銳的方式捅出了這些全球轉型中實際上早已存在、但遠未被解決的問題。
客觀地說,無論從縱向線性,還是橫向系統結構的角度看,無論從宏大目標,還是從實際上需要具備的推動全球轉型的物質基礎與思想心理條件而言,當代全球轉型都應該是一個遷延時日、相對漫長的歷史過程。但是,俄烏沖突這場經多年醞釀發酵的地區矛盾,在2022年升級為大規模軍事沖突後,使得全球轉型這一本來被認定的“漫長過程”迅速加快了節奏。沖突過程中各類潛藏矛盾被無情揭破,尤其是戰場上的生死博弈,與本來就廣泛存在的激進情緒相耦合,催化著更為廣譜的“決戰心態”。
上述“決戰心態”的動因來自各個方面:愛國熱情所推動、意識形態所驅使、現代傳媒所鼓動、戰略政策所激勵、黨派利益所使然。就俄烏沖突的當事方來說,即使在烏克蘭2023年的“春季反攻”失利並轉為“戰略防御”後,依然有相當一部分人不顧民族犧牲的巨大代價,呼籲在戰場上徹底戰勝俄羅斯。至於俄羅斯,在面臨西方集體打壓的巨大壓力下,曾有高層精英一再表示,不放棄動用戰術核武器以解救危局。直到普京明確表示,現在並沒有到生死存亡而需要動用核武器之時,這一輿論才逐漸告退。即便如此,俄方旨在以決斷方式對抗北約東擴推進的初衷並沒有改變。即使不能畢其功於一役,但也期待大大加速,並早日結束美國霸權。值得關注的是美歐的表現。俄烏危機發生後,歐美決策精英並非全無節制。但是,至少是在缺乏準確預判及周全謀劃的情況下,聽任危機步步升級,而不顧可能發生的巨大意外風險。這一點,早已為歐美輿論所詬病。其中,首先是國內選舉政治的考量,大大壓倒了對戰爭風險的客觀冷靜評估。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歐洲。當2024年初,美國黨爭迫使停止對烏援助之際,歐盟反而挺身而出,一舉通過了540億歐元的對烏援助計劃。歐盟此舉不僅在於尋求戰略自主,相當程度上,也以所謂“時代變遷”為理由,旨在通過對烏克蘭的支持,凸顯其早已準備擔當地區甚至全球領導、但迄今壯志未遂的這一政治抱負。為此,居然完全不顧經濟惡化與民眾抗爭,一反歐洲決策精英階層一向的冷靜與理性,鋌而走險。2023年《經濟學人》評論文章早已預見了這一趨勢,指出“現在歐洲才是烏克蘭最大的支持者,而不是美國。”[20]如此罕見的局面表明,俄烏沖突正是這種“決戰心態”的“助燃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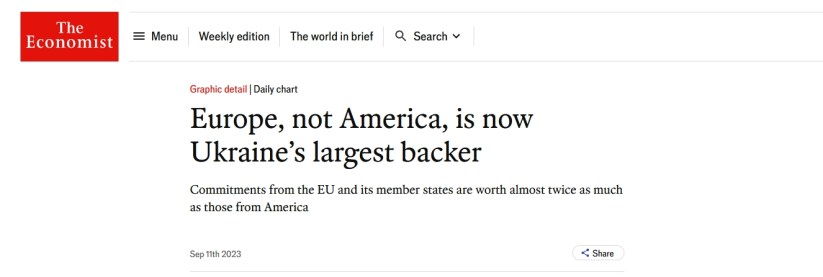
(二)沖突助推“再轉型”,而意識形態敘事扭曲這一進程
俄烏沖突的第二項重要影響在於,它的出現深刻作用於當代全球轉型的“再轉型”進程,但排他性意識形態敘事則甚囂塵上,對於全球輿論產生了負面幹擾,“再轉型”積極內涵被嚴重扭曲。
冷戰終結以來的全球轉型,在世紀之交,經歷了一次深刻的“再轉型”。
以筆者這一代人的經歷而言,“轉型”就是改革。從高度集權的政治經濟體制轉向市場、民主、法治為內涵的體制改革,乃是冷戰終結後幾乎所有計劃經濟國家的主要目標,學習西方是其主要內容。同時,當年也著重考察過原蘇聯東歐國家如何反思傳統體制,推進改革。這是四十多年前,中國俄羅斯歐亞研究學術領域之所以得以形成的一大起源。
到世紀之交,即20世紀90年代下半段以及21世紀最初幾年,改革還在推進,但環境在發生變化。當時,俄羅斯遭逢北約東擴,中國則遇到了台海危機;1997—1998年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與西方遊資不約而同作用下形成的東亞金融危機,事實上在俄羅斯也同步發生;而1999年美國轟炸俄羅斯盟友南聯盟,中國駐貝爾格萊德大使館也同時被美國導彈襲擊。總之,世紀之交的外部壓力推動著中俄不由自主地相互接近。
2001年,筆者當時在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高級國際研究院做訪問研究。當時該院歐洲系主任、美國歐洲問題權威學者戴維·卡萊歐(David Calleo)在一次談話中問我:“你老是說‘轉型’,那麽美國自己要不要‘轉型’呢?”事實上,當時不僅是戴維·卡萊歐,而且有一批美歐學者都發起了西方社會本身需要一場改革的呼籲,包括大量深刻嚴肅的學術批評。筆者豁然開朗,轉型竟是涵蓋西方、包括美國本身在內的一個全球過程。
“9·11”事件爆發,尤其是2003年伊拉克戰爭之後,西方社會的自我批評也在深化。但同時,美國新保守主義政治精英卻反其道而行之,高調主張弘揚意識形態,回歸西方傳統價值觀,並且以強硬手段在全球推廣民主,以此維護美國的地緣政治利益。在新保守主義支配下的美國霸權擴張,頗有點托洛茨基(Leon Trotsky)當年主張“不斷革命”的架勢,事實上,這兩者之間盡管南轅北轍,但還的確有著若幹思想史上的關聯性。“9·11”事件後不久,歐亞地區出現了一波又一波的“顏色革命”。如果說,1994年在俄羅斯與西方關系融洽的前提下,尚能簽署烏克蘭向莫斯科移交戰略核武器的《布達佩斯協議》。但到新世紀初多輪“顏色革命”博弈後,“轉型國家”學習市場與民主的初衷受到嚴重挫折。俄羅斯與烏克蘭這樣的國家雖都處於“改革轉型”進程中,但早在覆雜的國際環境之下分道揚鑣。毫無疑問,“顏色革命”是推動全球轉型“再轉型”的一大背景。

筆者清晰地記得,2003—2004年間,普京在國內推動加強中央政府權力,回收原來已給予地方的自主權,抓捕掌握了大量國家戰略資源的俄最大私企尤格斯總裁霍多爾科夫斯基(Mikhail Khodorkovsky)。大體與此同時,中國在2003年組建了國務院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規劃國企的海內外發展,同時出現了一場關於“國進民退”的經濟大辯論。顯然,這與20世紀80—90年代“學習西方”的總體氛圍相比,確有改變。中俄出現了強調自主性與開放改革相結合的“再轉型”。在此潮流播遷的背景下,地處歐亞東西方文明結合部最西端的烏克蘭,在東拉西扯之下,卻一步步向歐美靠近。
2020年代,隨著俄烏危機不斷惡化,“民主對抗威權”的冷戰式意識形態死灰覆燃,成為俄烏沖突中重建、擴大美歐軍事同盟的主要工具。2022年以後,隨著俄烏沖突升級為大規模軍事對抗,歐美話語占優勢的輿論又進一步將“民主與威權的對立”這一敘事廣為傳播,成為沖突相關國家動員國內、對抗俄羅斯的必備敘事,更使得意識形態的冷戰式對立似乎重回主流。
實事求是地說,歐美國家在幾個世紀的民主實踐中有著遠比非西方國家豐厚的積累,非西方國家學習與完善民主制度還有很長的路要走。但是,歐美各國具體的民主實踐並不等於都可以照搬到非西方國家。用福山(Francis Fukuyama)的話來說,丹麥與英國的國家制度“並不是任何國家都可以模仿做到的。”[21]雖然,非西方國家民主的構建也的確需要一定的外部條件,但這不等於說,民主可以強行從外部輸入。無論是民主還是集權,當各不相同的內部治理的“神聖目標”被用作為地緣政治工具進行外部擴張時,其結果一定是流血沖突與殘酷戰爭。一方面,危機頻生的國際動蕩時期,普遍出現的民族主義回溯、國家與政府權力重新強化的現象,如何使之避免引發與激化國際間紛爭,這不僅是在戰略與政策層面需加以把握調控,而且需要在理論詮釋方面得到進一步妥善改進。另一方面,當代歐美體制內部的亂象,嚴重扭曲了作為人類共同價值目標的“民主”、“自由”的本質與形象。在這樣的情況下還要一如既往地強行實施“民主輸出”,也實在是相當荒唐。

原則上說,筆者並不同意被稱為美國超現實主義理論家約翰·米爾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的“大國紛爭,必有一戰”的觀點。但是,在他看來,冷戰結束之初的美國單極稱霸時期,自由主義原則支配下的國家內部轉型尚可能得以推進,多極化發展態勢也可以容忍。但是,新興力量多極化趨勢一旦強勁崛起,本土的自主性與自由主義的“普世性”之間的緊張呈現,自由主義原則就勢必向歐美自身的國家利益與地緣政治利益讓步。某種程度上,米爾斯海默所說的自由主義若與民族主義、地緣政治相遇必定會一敗塗地的尖銳言辭,從一個側面道出了問題的關鍵。[22]
總之,世紀之交全球轉型過程中的“再轉型”趨勢,在俄烏沖突你死我活搏殺的場景下,被全面扭曲成了意識形態對抗性的敘事。對此,無疑應作出客觀理性的有力辨析。另一方面,也完全應該以此為契機,以加強和深化民主的切實並有效的實踐來進行回擊。
(三)沖突凸顯“深層結構變遷”,但國際力量對比依然互有進退,互相交織
俄烏沖突的另一個重要作用,是揭示出全球轉型中的“深層結構變遷趨勢”。總體上看,國際力量格局依然在對立中互相交織,攻守中互有進退。但諸多新現象的出現,推動著研究者們采用新的概念,或者拓展老概念的內涵,來對此加以詮釋。本文嘗試使用“半秩序”、“不選邊”、“大三角”、“轉焦點”等關鍵詞來表達經由俄烏沖突而顯露、並產生著重大影響的若幹深層次結構性變化。
- “半秩序”
俄烏危機首先揭示出的,乃是冷戰終結以來國際制度中的“半秩序”狀態。這種“半秩序”狀態,與世界戰爭和革命所帶來國際秩序變更的一個關鍵性區別,在於蘇聯解體和冷戰終結後的國際秩序變化,是在相對和平的條件下進行的。在戰爭與革命條件下,就像斯大林(Joseph Stalin)所說,坦克開到哪里,就可以在那里建立起自己的制度。但和平條件下的國際秩序轉型不一樣。
一方面,原有國際體制機制出現了大量變更甚至空白和灰色地帶。比如,最為關鍵的聯合國安理會機制還在發揮作用,但由於俄烏沖突中當事各方各執一詞,安理會的功能已被大大地削弱。包括曾經發揮協調與管理作用的國際機制,諸如歐安會功能、明斯克協議等都被一一邊緣化。
但另一方面,“半秩序”狀態不同於完全沒有國際體制機制發生作用的無政府狀態:國際體制機制構架仍然存在;大國間溝通管道並沒有被堵塞;國際危機管理有大量先例可供參考。最近的信息表明,國際社會各方尤其對世界貿易組織(WTO)、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世界銀行(WB)等關鍵國際組織恢覆各自的核心功能抱有殷切期待。而中國進出口銀行副行長張文才擔任世界銀行常務副行長兼首席行政官的最新進展,首先證明,推進國際關系制度化構建與改革符合大多數國家的意願。同時也表明,目前的“半秩序”狀態,實際上顯示國際組織體制的運行結構處於“半危機”狀態,不僅亟待改變,而且事在人為,也存在著推進改革的深厚潛能。
- “不選邊”
以金磚國家為代表的新興力量,很多是具有相當豐厚歷史傳統的文明古國,幾乎所有金磚國家和G20新興國家都曾經是歷史上雄踞一方的強者。國際大變局之下新興力量“第二次崛起”中的群體集結,[23]乃是當今國際力量結構的關鍵性特征,並與西方的相對衰落形成對照。新興國家不僅以前所未見的強勁勢頭推進經濟增長,而且表現出長期發展潛能。尤為引人注目的是,從2008年俄羅斯與格魯吉亞的沖突,到2014年克里米亞危機,一直到2022年的俄烏大規模軍事沖突,面對這一連串長期持續的沖突,絕大多數的新興國家、發展中國家采取了不結盟、不選邊的中立主義外交路線。他們不願意追隨歐美盟國,與俄羅斯對抗;同時,也明確反對戰爭,主張以和平方式與政治途徑解決沖突。正如《經濟學人》的文章所指出的,俄烏沖突中,就整個國際社會而言,占世界人口數量三分之二以上的國家主張不選邊、不制裁。這里首先是指金磚國家、上合組織國家、絕大部分東盟國家、以及其他新興經濟體與發展中國家。其實,就金磚國家而言,不單單是這一次不選邊、不制裁。例如印度,甚至早在1956年,當時的印度譴責美英出兵蘇伊士運河,但並不譴責1956年10月蘇聯出兵匈牙利。這是一個值得關注的國際史現象。總之,新興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奉行和平中立與不結盟立場有著深長的淵源。但是,與以往相比,它們在俄烏危機中的表現尤其顯示出在政治與安全領域迅速成熟起來的巨大潛能。
- “大三角”
從世紀之交以來的進程看,與上述變化密切關聯的是,大國間三邊關系、三角關系組合也呈現出從傳統大國均勢轉向倚重南方國家的客觀趨勢。[24]
隨著歐亞地區的沖突激化,歐洲國家曾希望借助俄、美、歐三邊互動發揮影響。比如,2008年美國拉烏克蘭、格魯吉亞加入北約,以期打壓俄羅斯。德法兩國出面阻止。稍後,俄羅斯與格魯吉亞的“五日戰爭”中,法國出面調停,旨在借美歐俄三邊互動,制約美俄對抗,以保持歐洲穩定。
而在另一方面,世紀之交以來,美國幾乎每一屆新政府上台都始終念念不忘通過聯俄制華,在美、俄、中三角關系的構架中占取優勢。[25]但在2016年以後情況驟然發生變化。2017年,美國公開同時把中俄作為競爭對手,表明它原先所期待的美、中、俄三角互動並不能如願以償。與此同時,俄烏沖突的升級,表明歐洲借歐、美、俄三邊互動謀取均衡的努力也告失敗。在此背景下,冷戰後一度活躍的俄、美、歐三邊關系與美、中、俄三角關系都變得相對凝滯

與此呈現反差的情景是,全球南方(Global South)成為各方爭取的重點。換言之,在參與重大沖突的對立雙方之間,南方國家已越來越成為舉足輕重的第三方。這是俄烏沖突後國際三邊關系領域的新現象。這里有兩種結構性趨勢:一種,在俄烏沖突的當事雙方處於對抗性狀態下,中國反對戰爭、尊重主權領土完整;同時,鑒於俄烏沖突事發所具有的“覆雜歷史經緯”,中方主張確保相互安全,反對追求單方面的絕對安全。這一組三方構架中,中國與絕大多數新興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站在一起。
俄烏沖突中呈現出了一個非常重要的三方關系結構變化的客觀趨勢,就是從原來還曾起作用的俄美歐三邊關系,在屢經挫折後轉向一個新的三方關系構架:即以美國為首的西方陣營支持烏克蘭與俄羅斯對峙,而包括中國在內的“全球南方”則持不選邊、不結盟、和平自主的戰略立場。這三方之間呈現出十分清晰的三足鼎立之勢。在這一總體背景下的其余三方關系,比如,中美俄、中歐俄、中美歐等多方組合也直接或間接地作用於上述關鍵三邊關系構架的變遷。
- “轉焦點”
這里的“轉焦點”指的是,與上述大三邊關系結構變化的趨勢相吻合,當代沖突與危機焦點正在從東向西轉移,而這與經濟政治重心向東偏移的情況,呈現出正好相反的趨勢。
在近年俄烏沖突持續的同時,哈以沖突爆發,台海局勢緊張,這成為全球三大最主要的沖突熱點。以往西方列強在歐洲保持著戰略均衡,而借在亞洲制造、推動戰爭與沖突來維持均勢。就像20世紀50—60年代,西方列強在歐洲維持均勢,但卻在亞洲發動朝鮮戰爭和越南戰爭,以在亞洲的伸展博弈來維持在歐洲的均衡。但現在的局面不一樣。這一次,人們看到的是,比如,盡管民進黨在中國台灣地區選舉中獲勝,但不僅美方明確表示反對“台獨”的政策不變,中國大陸在表示堅決反對“台獨”的原則立場的同時,以盡可能克制的態度對此做出反應。這預示著兩岸之間盡管依然存在著高度敏感的態勢,但並不是完全沒有可能在今後一個階段中防範擦槍走火、乃至於更大規模的風險。這里所顯示的一個明顯反差是:與以往正好相反,亞洲地區暫時保持著和平狀態,但是,歐亞地區的俄烏沖突與中東地區哈以沖突卻沖突難止、戰火不斷。這一新格局在相當程度上揭示:一方面,舊金山元首峰會後的中美關系,有可能在一個階段中使中美兩國避免對抗性沖突。而中美關系即使是暫時的穩定,都是有利於整個亞洲的安全與發展的。另一方面,作為目前階段的輿論和人心之所向,即使其他地區戰亂不定,但是,作為當下與今後世界經濟增長的主要依托,亞洲不能亂。
總之,亞洲相對地維持穩定,歐亞與中東則繼續動蕩。就區域格局對照而言,這表明沖突焦點的偏移。而從深層次上的力量對比來說,這是權重轉移的一個標志。
(四)沖突推動向“複數全球化”的轉化,但脫鉤斷鏈威脅仍在
於爾根·奧斯特哈默在他的著作《全球史講稿》中,第一篇文章就開宗明義地提出:認為全球化具有劃一而明確的定義,“這是一個不現實的假設”。據此,他在闡述20世紀90年代以來有關“全球化”概念的變化時指出:到2016年,與以往全球化進程相反,普遍出現的是“碎片化和去全球化趨勢,民主的倒退和世界上許多國家新出現的強勢的民族主義”。因此,奧斯特哈默提出,“全球化這個詞往往要理解成一種覆數”[26]。如果說,在奧斯特哈默看來,2016年對於全球化的理解是展開了一個新的階段的話,那麼,在該書成書四五年後,俄烏沖突大規模爆發的2022年應該被視為是單數的“全球化”轉變為一種“覆數”全球化進程中值得關注的特殊時刻。
被俄烏沖突大大強化的“複數全球化”現象有幾種表現形式。
第一,俄烏沖突以及隨後西方嚴苛的對俄制裁,造成歐亞地區乃至更大範圍內的傳統產業鏈、物流鏈、金融鏈的大面積中斷,同時也催生著新產業形態的打造、新貿易通道的開發、新支付方式的采用、新區域合作方向的開拓。一方面,以遠東西伯利亞開發開放為支點,以俄羅斯整個經濟東移為標志的地緣經濟格局的重組,並不局限於俄羅斯與中國,而是包含著中東、中亞、南亞、東南亞廣大地區。這樣一個宏大地緣經濟新格局的形成,與傳統全球化的超越國界主權的做法不一樣,將會更多地強調主權,堅守本土利益。這意味著上述廣大地區與國家將在既要對外開放、又要維護主權,比以往全球化進程更為複雜多樣的局面下推進區域與全球合作。這將是一個更為艱難的嘗試改革的過程。另一方面,在全球化遭逢挑戰、不得不改弦更張的情況下,首當其沖的俄羅斯,究竟會是退守“堡壘”、隔絕交往,還是盡一切可能繼續與世界大市場保持聯系?從2023年6月聖彼得堡經濟論壇的情況來看,即便是在當時如此艱難的條件下,普京都不願意開歷史的倒車,他公開宣布決不走原蘇聯封閉鎖國的老路,而是主張繼續開放。20世紀90年代筆者在莫斯科專家研究所進行合作研究時,曾有機會觀察過當時的優秀青年專家納比烏琳娜(Elvira Nabiullina)的工作狀態。現在她作為俄羅斯央行行長,首先堅持以市場經濟的方式,維持俄羅斯經濟運轉,而她背後的最大支持者,就是俄羅斯總統普京。這可視為在俄烏沖突沖擊背景下“覆數全球化”的一種表現,盡管,這還僅僅是一種大國立場的表達,還沒有在全球範圍真正得以實現。
第二,俄烏沖突爆發之後,遍及歐洲的能源危機,以及給發展中國家帶來的糧食危機,引起了極大的恐慌。在人們對2016年出現的‘特朗普現象’記憶猶新、驚魂未定之際,這一波新的動蕩又給疫情尚未終結的世界市場帶來了巨大沖擊。此後,隨著俄羅斯能源供應的重心從歐洲向亞洲的轉移,以及與中東地區加強合作,特別是俄方宣布以盧布、而不是以美元、歐元結算能源交易,似乎意味著一個以能源大宗商品為錨定物基礎的新的國際貿易結算方式正在以出乎意料的方式打探未來的格局和發展路徑。與世紀之交的歐元問世,以及稍後日元一度試圖對以美元為核心的國際金融體系發起的挑戰相比,俄烏沖突帶來的國際貨幣格局的變化,雖還遠沒有經過充分的準備,規模也相對有限,但是,對未來新興國家的國際貨幣合作帶來了富於想象力的期待。繼能源之後,俄烏危機以來得到提升的主要發展中國家,尤其是金磚國家間糧食貿易與自給自足水平的提升,在多大程度上將會帶來非美元貨幣結算規模的相應擴大,也引人注目。在美元依然保持強勢地位的背景下,在此之外的多種貨幣國際合作網絡的形成,可視為“覆數全球化”現象正在逐漸形成之中的另一個側面。
第三,作為“單數全球化”進程的關鍵部分,全球性的減排去碳進程,要求各國減少使用傳統能源的比重。然而,俄羅斯作為能源輸出大國,是依靠油氣貿易所獲頂住制裁狂潮的。這一情況將深刻作用於俄羅斯的減排進程。此外,危機中歐洲各國甚至重新啟用了包括煤炭在內的傳統能源,而作為世界LNG第一出口大國的美國,依靠LNG出口支撐經濟穩定增長,也不是一個短期的需求。可見,正是俄烏沖突,包括由此而實施的西方對俄羅斯的全面制裁,推動形成了減排去碳的“單數全球化”與繼續維持傳統能源經濟的逆向的“覆數全球化”之間的又一層緊張關系。
總之,從“單數全球化”走向“覆數全球化”,本身是一個非常複雜的過程。俄烏沖突所揭示的,不光是“華盛頓共識”下的“單數全球化”與多極化趨勢下的“複數全球化”之間的對立,而且,“複數全球化”並非就是“單數全球化”的逆反,有些僅是某些區域、某些領域的重新啟動與配置組合,兩者之間存在著覆雜互動。此外,問題在於,由敵視帶來的隔絕與脫鉤,不可避免地還將存在相當長的時間。

根據上述變化,筆者的初步判斷是:
第一,俄烏沖突陷入對峙局面,折射出與此有關的全球力量格局進入了一個互有攻守但又互相膠著、各有千秋卻又高下難分的總體相持階段。
在這樣的相持階段,至少有兩方面的問題值得關注:一方面,“人類文明共同體”的觀念明確地宣示:當今時代已不是一種意識形態取代另一種意識形態、一種文明取代另一種文明的時代。當年的蘇共二十大也曾提倡過“和平共處”,但是未能避免在聯合國大會上敲皮鞋,也未能避免古巴導彈危機。歸根結底,還是在於沒有避免“相互埋葬意識”。因此,如果真正立足於“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並切實付諸實踐,雖必定還會經歷不可避免甚至是非常殘酷的博弈,必定還會面臨一波又一波驚濤駭浪的沖擊,但是經過長時間努力,最終還是存在著“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機會與可能。另一方面,中國抗日戰爭期間的正確戰略路線迄今留下深刻的歷史啟示。老一輩專家學者常提及,他們的同代人中很多人正是讀了毛澤東的《論持久戰》,理解了當時既不可能走速勝路線,更不做投降派,從而以堅忍不拔的打持久戰的決心,毅然投身抗戰。時移世易,但在面臨前所未見的強勁挑戰,需要對若幹種可能的前景做出重大選擇之際,《論持久戰》的原則依然是我們的重要理論與戰略思想依據。
第二,以朝鮮戰爭的邏輯而告終,乃是俄烏沖突的可能前景之一。
一年半以前,我曾經試圖把戰爭與俄國內體制轉型相關聯加以觀察:一方面,從兩百年左右的歷史看,如果說每次世界大戰(1812年歐洲反拿破侖戰爭、一戰、二戰)總以俄蘇獲勝告終(一戰中蘇聯的脫穎而出也可視為一次重大成功),然後國力增長,國際地位上升的話,那麼,與此相反的另一方面就是,兩百年來,俄國與周邊的戰爭幾乎都遭遇失敗,並激起了俄羅斯國內的重大改革。比如,19世紀50年代克里米亞戰爭失敗,導致1861年農奴制改革等延綿多年的重大變化;1904年日俄戰爭失敗導致1905年憲政改革;1920年波蘇戰爭失敗,間接地導致1921年新經濟政策的問世;1979年阿富汗戰爭導致戈爾巴喬夫改革,等等。當時我是嘗試對戰爭與國內轉型兩者間的相互關系作初步的邏輯推演。但俄烏沖突的情況卻更為覆雜。事實上,戰爭史上也沒有任何一次大規模國際戰爭可以作簡單類比。問題之一,俄烏沖突既是周邊沖突,但又伴有明顯的全面對抗的背景。因此,這一場沖突的結局可能會勝負參半。問題之二,盡管俄羅斯在戰場上已扭轉頹勢,但它所面對的整個北約是否會心甘情願地公開接受這一事實?當下的歐盟繼續大規模支持烏克蘭堅持對抗,以及美國將於今年春季也緊跟發布新的對烏援助的總體方案,就說明,戰爭在2024年有可能延續,直至美國大選。問題之三,2024年不僅是幾乎所有當事國的大選年,而且一批利益相關的國家也將面臨大選。這些因素必定以各種方式影響俄烏沖突的發展軌跡,各種可能都會出現。即使沖突雙方以類似朝鮮戰爭的方式收場,也即俄烏雙方(實際上是俄與北約)以停止戰爭並長期擱置最終勝負為終局的話,那麼,是否會導致俄羅斯社會出現一種與前述兩種情況都不一樣的發展趨向?是否會出現沖突之後既不是國力大增、地位提升,也不是失敗背景之下激起國內的重大自由化改革,而是比較長期地延續目前的體制狀態,以所謂不同內涵的“威權主義路線”,在盡力維持穩定與安全的前提下,既不會回到高度集權的原蘇聯狀態,也不會走向西方民主;既不會完全封閉,甚至還會在十分艱難的條件下追求開放與合作,但也更加不會回到20世紀90年代那種“放任式自由經濟”?或許,會在相對較長的時間內在上述這兩種可能之間徘徊移動。當然,需要說明的是,俄烏沖突以朝鮮戰爭的方式結束只是一種基於邏輯推演的假設,不排除在各種突發因素的作用下的更多選項,包括這一沖突迅速擴大規模而失去控制的可能性。
第三,俄烏沖突也襯托出,中國選擇不結盟、不選邊、公平正義、和平發展的外交路線的明智與遠見。
俄烏沖突爆發後,一個討論很多的問題是,面臨當今拉幫結派的狂潮,中國是否只能以結盟對抗的方式相抗爭。問題的另一面是,鑒於四十年改革開放的巨大成就,以及延續至今的中國與歐美之間規模巨大且影響深刻的經濟、科技、社會、人文等諸方面聯系,能否回到20世紀末那個被稱作為“韜光養晦”的年代。從俄烏沖突的表現看,中國既沒有輕易地走向結盟對抗,也沒有重新“韜光養晦”。中國在嘗試走一條既是獨立自主、不結盟、但是恪守原則,最大限度地將本國意願與國際和平、安全、公正、穩定相關聯的戰略路線。與匆忙走向結盟對抗、或簡單主張回到80年代相比,選擇走上述第三種路線,肯定會經受更多覆雜環境的考驗,操作上也因更為細致微妙,顯得更艱難。但是,放眼長時段,以中國目前的國際地位和所應承擔的責任,以中國目前所擁有的能力來看,這是一個更為允當的歷史性選擇。二十世紀之初,日俄戰爭在中國領土上爆發。當時的中國在外交上也持“中立”立場,但腐朽的清政府根本無力御強敵於國門之外,只能容忍強鄰在自己的國土上廝殺。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前夕,國民黨政府也曾考慮過采行“中立外交”。蔣介石在1945年1月的一篇日記中就寫道:“若我能自立自主,中立不倚,則彼(筆者注:指蘇聯)當能尊重我中立地位。”[27]但蔣政府的中立外交路線設想,在當時國力不濟、列強紛紛插手的情況下,根本沒有實現的可能。新中國建立以後,經過“一邊倒”時期的經驗教訓的總結,也經過“文革”非常時期的考驗,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伴隨著改革開放的推進和國力的不斷增強,中國外交真正走出了一條獨立自主、公平正義、不結盟、以和平發展為目標的廣闊道路。獨立自主的不結盟政策,並非等同於簡單的“中立”。而且,這看似僅僅是外交路線,事實上,這也是在全球轉型覆雜進程中的路徑選擇問題。中國力求通過確保安全、利於發展、主持公道、和平共贏的方式,既確保自身權益,也力倡萬國開和平。
三、中俄合作與“亞洲地中海”的未來構想
中俄合作需要在全球轉型的關鍵領域與核心地區表現出它強勁深刻的穿透力。“亞洲地中海”就是這樣一個能夠體現當前中俄合作高度與前瞻性的重要構想。

20世紀末,法國經濟學家吉普魯(Fraancois Gipouloux)曾經提出“亞洲的地中海”的概念。他認為,發展中的西太平洋地區——具體地說,指的是從日本海至馬六甲的西太平洋廣大沿海國家與地區,可以像歐洲地中海一樣,不光可以通過長期經濟繁榮發展推動各國合作,而且可以在政治、社會、文明構建等各個領域為人類作出貢獻。吉普魯教授當時還應邀在華東師大做了講演,他的題為《亞洲的地中海》的專著也已經翻譯成中文出版。[28]
面對亞太地區拉幫結派(奧庫斯、印太四國、五眼聯盟、包括北約欲染指亞洲)的挑戰,在不放棄加強國防以抵御外敵的前提下,還必須發揮地緣經濟的巨大優勢,以盡可能的合作抵御對抗,以共贏爭得民心,以包容開放的區域構建為著眼點,為擺脫當下危機尋找新的突破口。吉普魯的“亞洲的地中海”的構想具有這樣的一種功能:它貼近國際轉型所面臨的問題,連接各方的戰略需求,符合全球與區域多方發展的綜合利益。當然,為實現這一目的,各方必將付出極其艱苦的長期努力。
推動“亞洲地中海”這一構想的客觀依據在於:第一,俄烏沖突後,俄羅斯經濟重心決心向東轉移的戰略安排,為亞太地區的區域化構建,提供了新的因素和十分重要的機會。同時,亞洲地區長期增長態勢為全世界所看好。而亞洲今後在長時段中所需要的能源、糧食、環境、農產品、潔凈水等大宗物資,以及需要一個有待開發的廣大市場環境,而俄羅斯當屬最為便捷的來源地之一。俄羅斯與西太平洋國家之間存在著互補合作的巨大機會與空間。
第二,當今世界在中美緊張對峙的同時,還存在著一個廣大中間地帶。包括在安全與經濟方面還不得不兼顧兩頭的大多數中間立場國家。近年來,中國在亞太地區的外交推進表明,如果運籌得當,還可能爭取到與已被美國拉上戰車的國家互利合作的機會。王毅外長最近提出的推動中日韓自由貿易區談判的重要倡議,就可以看作是一個標志性安排。這說明,遏制亞太地區一些國家攜美遏華的態勢,需要從政治與地區安全角度應對,同時,也完全有必要運用經濟杠桿來求破解。甚至,客觀地說,中美關系的穩定也對這樣新的地區構建有著期待與需求。
第三,不僅俄羅斯與亞太地區之間合作有待加強,而且,隨著氣候條件的變化,北極航道的開通,又使得西太平洋地區有可能通過歐亞大陸的北方通道,與歐洲之間開展往來。筆者所在的俄羅斯研究中心在前十余年曾參與一個有俄羅斯、挪威、新加坡、韓國、日本、後來還包括德國學者參加的“最後的邊疆”的多國研究項目,延續多年對這一研究項目的參與,使筆者感受到各國學者專家對經過北方航道連接歐洲與西太平洋地區經濟的巨大熱情。雖然,俄烏沖突使國際局勢覆雜化,但俄羅斯經濟向東方轉移,遠東西伯利亞的開發開放,加上北方航道的逐步開通,從長期而言,提供了一個難得的推動歐亞合作的戰略機遇。
第四,2021年以後一個非常重要的變化,乃是《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系協定》(RCEP)所確立的區域合作框架。這個以東盟為主導、中國積極協助其開展合作的區域板塊,有著發展與北方夥伴合作關系的多年積累。而若幹年以來俄羅斯也在東盟國家深入發展關系。無論在經濟、政治、科技、防務等方面都取得了引人關注的進展。當前全球化的低潮時期,需要有像“亞洲地中海”這樣的地區構建,從區域合作出發,來重新激發全球化的動力。特別是在不同地區合作機制出現的背景下,提出“亞洲地中海”的概念構想,有助於推進《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系協定》(RCEP)進程。換言之,如果能夠在北方的俄羅斯與南端的東盟之間構建起一片有效的經濟合作地帶,不言而喻,對地處南北之間的中國而言,就能夠相當程度上改善周邊地緣政治環境,就有了更大的進一步推展多面向合作的基礎與空間。因此,“亞洲地中海”是當下我們從全球轉型和經略歐亞的大局出發、重新估量對俄合作戰略地位的一個可供選擇的長遠抓手。
第五,今後中國的內外經濟循環,將從以往四十年以歐美市場為主導,逐漸地演變成為在力爭保持在歐美市場份額的同時,在大陸歐亞以及西太平洋地帶尋找戰略支點,以平衡、補充在歐美市場的缺失。“一帶一路”倡議的初衷,就是希望在歐亞大陸西向運籌,從而找到戰略突破口。多年以來,盡管“一帶一路”倡議在其他各方面都有推進,但是,俄羅斯與帶路的對接,還存在著可以大幅度提升的空間。中俄不僅可以向歐亞大陸縱深地帶發展,而且可以在推動俄羅斯與西太平洋地區國家發展合作方面發揮重要作用。中國東部沿海地區的進一步經濟發展與安全保障,也需要有“亞洲地中海”式的合作來提供機會。無論是圖們江出海口的取得,無論是從渤海灣南下到整個中國沿海空間的發展;也無論是兩岸與南海的穩定,俄羅斯因素的參與都將是勢所必然的趨勢。從形式上看,這是從經濟著手;但隨這一局面發展而來的,將有可能是整個地區的安全機遇與穩定空間。
就中國東部沿海地區的發展而言,東北圖們江地區原來就有著對俄羅斯合作的良好基礎,“亞洲地中海”的總體推出,勢必有利於中國東北地區口岸條件的改善。隨著中俄產業聯合開發在東部沿海地區的推展部署,中國東部沿海地區,特別是江蘇東部沿海地區的大型深水港口建設的環境也正在迅速得到改善。作為南北海域通道的必經之地,對未來俄羅斯與西太平洋南部地區合作發展而言,這是已初具規模的良好基礎設施條件。早在2007年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參崴)已經是黑龍江的內貿貨物中轉口岸,令人欣慰的是,2023年5月,海關總署同意吉林省增加俄羅斯符拉迪沃斯托克港(海參崴港)作為內貿貨物中轉口岸,這是中俄合作的一個重要進展。
盡管俄烏沖突仍未停息,亞太地區原有合作紐帶正面臨脫鉤斷鏈的嚴峻挑戰,而且上述相關各方合作意向與潛能的發掘遠非輕而易舉,而是一個長期而艱難的開拓過程。但是,以“亞洲地中海”為目標的中長期目標的未來區域構建,不僅將為中俄合作帶來新機會,而且,通過西太平洋地帶的穩定發展,還有望為整個跨太平洋地區,乃至於給整個全球轉型進程活力與空間。
注釋:
- [美]亨利·基辛格著:《世界秩序》,胡利平、林華等譯,北京:中信出版社,2015年,第24頁。
- 同上,第3頁。
- 2019年底,在尼爾·弗格森訪問上海期間的小型座談會上,筆者就其所著的《基辛格傳》向弗格森先生提問:為何將基辛格稱作為“理想主義者”,而不是一般所言的“現實主義者”。弗格森博士專門就此做了詳盡回答。
- 根據布羅代爾、沃勒斯坦、阿里吉著作觀點的綜述性表述,具體內容可參見[法]費爾南·布羅代爾著:《15至18世紀的物質文明、經濟和資本主義》,顧良、施康強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7年;[美]伊曼紐爾·沃勒斯坦著:《現代世界體系》,郭方等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年;[意]喬萬尼·阿里吉著:《漫長的20世紀:金錢、權力與我們時代的起源》,姚乃強等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2年。
- [美]伊曼努爾·沃勒斯坦著:《現代世界體系》(第一卷),郭方等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年,英文版第一卷序言第2頁。
- [美]伊曼努爾·沃勒斯坦著:《現代世界體系》(第一卷),郭方等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年,英文版第一卷序言第2-3頁。
- 同上,英文版第一卷序言第6-7頁。
- [意]喬萬尼·阿里吉:《漫長的20世紀:金錢、權力與我們時代的起源》,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2年,第13頁。
- [意]喬萬尼·阿里吉:《漫長的20世紀:金錢、權力與我們時代的起源》,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2年,第473-474頁。
- [德]於爾根·奧斯特哈默著:《世界的演變:19世紀史》,強朝暉、劉風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6年,第4頁。
- [德]於爾根·奧斯特哈默著:《全球史講稿》,陳浩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21年,第12頁。
- [德]於爾根·奧斯特哈默著:《世界的演變:19世紀史》,強朝暉、劉風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6年,第101頁。
- 同上,緒論第4頁。
- [德]於爾根·奧斯特哈默著:《全球史講稿》,陳浩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21年,第140頁。
- [英]巴里·布讚,喬治·勞森著:《全球轉型——歷史、現代性與國際關系的形成》,崔順姬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249-276頁。
- Andrei P. Tsygankov, “From Global Order to Global Trasition”, Russia in Global Affairs, 2019, Vol.17, No,1, https://eng.globalaffairs.ru/articles/from-global-order-to-global-transition/
- 馮紹雷:“歐盟與俄羅斯:為何從合作走向對抗”,《歐洲研究》,2015年第4期,第43-66頁。
- 普京於2023年10月5日在瓦爾代論壇上的講演,筆者在場聆聽了他的這篇講話。Cм. Заседание дискуссионного клуба «Валдай». 5 октября 2023 г. http://www.kremlin.ru/events /president/news/72444
- “奧巴馬在西點軍校2014年畢業典禮上的演講(雙語)”,2014年5月30日,https://language.chinadaily.com.cn/news/2014-05/30/content_17555058.htm
- “Europe, not America, is now Ukraine’s largest backer”, September 11, 2023. https://www. economist.com/graphic-detail/2023/09/11/europe-not-america-is-now-ukraines-largest-backer
- [美]弗朗西斯·福山著:《政治秩序的起源:從前人類時代到法國大革命》,毛俊傑譯,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4年,第425頁。
- 參見[美]約翰·米爾斯海默著:《大幻想:自由主義之夢與國際現實》,李澤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
- 關於世紀之交新興國家群體上升被稱為“第二次崛起”,乃參照華裔學者熊玠的提法,特此說明。
- 在討論該問題時,研究者常常在相同語境中同時使用“三邊關系”和“三角關系”兩組概念。在筆者看來,“三邊關系”主要指俄美歐這種三方之間有著專有工作框架的關系,比如,冷戰之前曾有的“歐安會”,以及在冷戰結束後一直存在的“歐洲安全合作組織”。但是,像中美俄之間並不具有這樣調處三方關系的專有工作框架,卻又實際上發生著相當重要而又微妙的互動,故在此處選擇沿用原有的“三角關系”的說法。需要說明的是,這里的“三角關系”並非專指具有對抗性沖突的這樣一種大國關系。
- [美]詹姆斯·戈德蓋爾、邁克爾·麥克福爾著:《權力與意圖——後冷戰時期美國對俄羅斯政策》,徐洪峰譯,北京:社會文獻科學出版社,2017年,第380-384頁。
- [德]於爾根·奧斯特哈默著:《全球史講稿》,陳浩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21年,第9-15頁。
- 蔣介石:《蔣介石日記》,“1945年中心工作”,1945年1月;47.48.49.General,Volume 1,美國胡佛研究院檔案館。
- [法]弗朗索瓦·吉普魯著:《亞洲的地中海:13—21世紀中國、日本、東南亞商埠與貿易圈》,龔華燕、龍雪飛譯,北京:新世紀出版社,2014年。
轉載自《觀察者網》,本文首發於《俄羅斯研究》2024年第1期
























